解读习时代党政机构变革 戊戌年中国迈入体制驱动时代
这个戊戌年的中国政治注定不平静。
当关于中国“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制的讨论稍显平息之后,北京时间3月13日,中国政府正式公布了新一轮国家机构改革的具体内容。这一轮改革方案,将在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布满红星的穹顶下,由近3000名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审议并通过。与1998年朱镕基进行国务院改革之后,历次中国大部制改革都会在正式消息公布前进行轰轰烈烈的讨论不同,此次中国要进行“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消息,在2月底才向外界公布,方案的透露到通过,用时不足一月,突兀,但是中南海显得胸有成竹。
从具体改革内容来看,所有的细节似乎都在证明,作为中国历史周期进入习近平时代后的一次大规模的改革,其轨迹和目的与过去20年的几次所谓“大部制改革”截然不同,其目的服务于中共“两个一百年”,时间坐标指向2035年中国基本实现现代化和2049中共建国100年,可以将其视作习近平“第五个现代化”中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具体呈现。
靴子落地,这一轮机构改革意味着在“习时代”,改革2.0版的时期,中国的国家机构开始试图去重新匹配时代的跃迁和发展要求,包含政府体制,社会运行,政企关系,央地关系等诸多要素开始重构,改革再度进入体制驱动的时期。
改革动因:“构建强有力的领导结构”
多维新闻此前在《中共三中为何首度提前召开?三大解读习近平机构改革》对于习近平为何要在此时推动新一轮中共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有过解读,认为改革的关键原因在于“面对新时代新任务提出的新要求,党和国家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同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同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这一点在中共十九届三中决议,李克强关于国家机构改革的说明报告,以及近日中共政治局委员丁薛祥、刘鹤在《人民日报》上的文章解读,已经有了清晰的答案。

但是这个“答案”只是第一重。更深一层的改革动因,在习近平的意识中,对于当下的中国来说,如果继续保持中共政权的稳固和改革发展的深入,领导结构的坚强有力在既定情势下是首要环节,领导结构包括执政党体系和领导核心两个主要部分,这也是现任政治局常委,有“三朝帝师”之称的王沪宁早期重要的政治观点。他认为,“现代各国的社会发展雄辩地证明,强而有力、组织严密的政党系统及其核心是社会走向现代化的重要组织保证和体制资源”。
从2012年中共十八大以来习的布局来看,其实就是在围绕这两个因素在布局,反腐,整党,“习核心”,修改国家主席任期,以及机构改革,所有这些影响、波及中国的重大举措背后,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体系和核心,是最根本的动因。这个核心,毋庸置疑,是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而体系则是一个更为复杂的概念,简要的理解就可以视为“党和国家机构”。
重构改革 体制驱动
这次中共进行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之后,或许可以做一个初步的定论,中国的改革开放再度进入了“体制驱动”的时代。
从历史上来看,过去40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历程,离不开体制驱动。
朱镕基从1994年至1998年间推动的历次改革,都是在认识到以机构为主要构成的中国政治体制,与国家社会快速发展之间存在矛盾后而推行的。可以说,过去40年的中国改革开放史,也是一部中国体制改革史,中国政府一直试图让国家治理体系匹配国家发展的努力与尝试。整体而言,政府部委系统不断适应新时代形势环境的变化,渐趋精简和高效。
从1978年邓小平在中国推行改革开放之后,时至今日。今天中国社会方方面面的局部改革已使社会调控体制的建设正处在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上,各项局部的改革已经达到自己的定点,新引发的矛盾和问题必须通过总体性重构方能得到解决。这也是王沪宁此前在《中国九十年代的战略抉择》一论文中秉持的观点。对此他给出的药方是重构中国社会调控体制的战略时机已经成熟,现在中国迫切需要的是构想出整个社会调控体制的总体再构原则和蓝图,以将十余年来积累的局部改革总结成总体机制,并平衡各局部改革之间的差落。现在需要做出的选择是,形成新的有效的体制,构建中国九十年代之后乃至下个世纪现代化进程的体制保障。
一个好的体制,能够焕发这个国家的生机和活力。其中尤其是一些政府机构,设立得当,不仅不会如传统西方学者观点那样禁锢改革,反而能够有效推动改革深化,例如早期的发改委。
当然,王沪宁当时只是以一个学者的身份在进行学术探讨。政治的现实表明,尽管江泽民和胡锦涛时代,中国领导人也一直在试图建立一个新的“有效体制”。但是或是因为现实阻力太大,或是因为领导人威权不足,作为体制中的重要一部分的机构改革,往往不能毕其功于一役,虎头蛇尾,草草了事。所以中国也就一直无法重新进入“体制驱动”的时代。今天习近平对于中共这个政党和中国的国家机构进行梳理,恰是表明此番要义。
从裂变到聚变
在目前出路的改革文件内容中,一个关键词就是“整合”。例如组建自然资源部,不再保留国土资源部、国家海洋局、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组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不再保留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不再设立国务院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组建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不再保留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40年之前,无论是国际局势还是中国内部事务,作为中央政府,其面临的事务和挑战,与今天截然不同。随着改革的深化,政府要应对事务的增多,很多机构就不断增设,例如网信办,例如发改委。这个过程是一个国家治理体系“裂变”的过程,负面效应就是机构与人员越来越臃肿,因此从朱镕基时代开始,如何给机构“减负”,进行“大部制改革”就成为摆在历届总理案头的命题。
尽管从1998年之后,中国进行了多次“大部制改革”想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要认识到,“聚变”绝非简单的把机构裁撤与合并在一起那么简单,其关键在于机构的职能。这也是为什么此次机构改革中国政府没有再打出“大部制改革”的说法,而是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到了职能的重组,合并,以应对时代发展。
改革“钱袋子”
政治运行的因素中,人权,事权,财权三者为关键,其中尤以财权为重中之重。这也是为什么朱镕基在1994年进入中央,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后便进行财税改革,以分税制为切口,确立延续至今日的中国央地“强中央,弱地方”二元关系。因此衡量一次国家机构改革是不是真的“动刀子”,关键性指标就是看动没动“钱袋子”或者“管钱的人”。
从目前中国官方公布的内容看,一行三会的改革,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隶属关系的调整,改革国税地税征管体制,都清晰的表明这次改革将会对“财政赋税金融”领域进行大规模调整。
央地关系重构
这次改革方案透露的第五个“关键信息”是中国央地关系将全面重构。在中国,中央和地方关系是中国社会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环节,有经济意义,更有政治意义。
从中央到地方的政府间财政关系看,存在着财权与事权高度不匹配问题,即是说中央政府收走了大部分的税收,但支出责任多半留给了地方政府,越到基层政府,支出责任越重而财力保障能力越差。二十余年间,地方财政收入仅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约为45%,但财政支出却占全国财政总支出的约70%以上,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政令不出中南海”现象。其次,分税制下地方财源受到挤压,使得地方政府高度依赖土地出让收入,土地财政又推高了房价,高房价在2010年以后几近失控,使得民怨沸腾,成为近年来中共面临的棘手民生和经济问题。同时,房价畸高下的资产泡沫的不断放大又加剧了经济和金融风险。再次是转移支付制度不完善,中央将大部分税收持于手中,应转移到地方的那部分从来不与地方讨论,不接受监督,而是以“项目建设”的方式落实,投资及决策权力集中于国务院的发展改革委员会及各大部委,地方政府毫无话语权,只好在北京设立“驻京办”,出现了所谓“跑部钱进”的恶劣局面。但是,伴随着地方财政水源不足情况,政治上的“山头主义”又频频发生。
对于以上情况,中共决策层不会不进行反思,在中共十九届三中公报中,所说的“统筹优化地方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构建从中央到地方运行顺畅、充满活力、令行禁止的工作体系。科学设置中央和地方事权,理顺中央和地方职责关系,更好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中央加强宏观事务管理,地方在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前提下管理好本地区事务,合理设置和配置各层级机构及其职能”,尽管看上去是中共枯燥的官方语言,但是行文中无不透露对于当前中国央地关系矛盾的反思和构想。
以上只是对于此番中国机构改革蜻蜓点水的解读,因为国家机构改革信息透露尚不完整,中共党的机构改革也未揭开面纱,相信更多的变革,将在不久之后陆续到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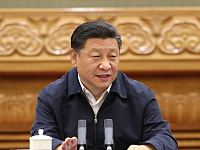






 +61
+61 +86
+86 +886
+886 +852
+852 +853
+853 +64
+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