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元吃住,30元买性服务”:在深圳最堕落的地方,年轻人集体等死(组图)
毫无盼头的人生是什么样?
如果非要总结,我想答案大概是: “一切皆可放弃”。
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放弃了生计、身份、尊严、所有社会关系,
在高歌猛进的城市角落打造了一处堕落天堂。
同时,他们也被滚滚向前的时代车轮无情碾过。


深圳,距离市中心不到10公里的龙华新区,有一个叫做三和人才市场的地方。

这里常年游荡着一批被称为“三和大神”的人。
他们共同信奉着“做一天工,阔以玩三天”的精神信条。

打工永远只找日结,赚得百来块工钱后,便开始实践“吃喝嫖赌抽”五字真诀。

不论当下物价如何攀升,在三和,生活成本被压缩到了极限水平。
大神们手提蓝白大水,抽五毛一根的红双喜散烟。

花2块钱,可以吃上淋着古怪颜色酱油的肠粉;再加3块,就能来碗飘着青菜,偶尔能发现肉丝的挂逼面。

吃饱喝足后,大神们钻进昏暗污浊的网吧,追逐各自的精神家园。
1块5每小时,8块钱通宵,地球不爆炸,他们不挪窝。

结束了游戏里的腥风血雨,一排人呼呼大睡,东倒西歪,宛如丧尸。

想睡得有仪式感点,花个十几二十块便能喜提床位。
30平米的简陋房间,密密麻麻地摆满双层铁架床。空气里弥漫着汗臭与尿臊味。

被褥枕头许久未换,臭虫陪睡也是常有的事。
但对大神而言,只要能充电、有WiFi,这些都不是问题。

人才市场附近,龙华公园的隐蔽处,30—50元就可以潦草地解决性需求。
三和人管这叫“修车”。

眼看钱花得差不多了,大神们不得不开启高阶修炼模式。
天为被,地为席。
海信人力资源市场,每到晚上,都会变成“海信大酒店”,床位供应十分紧张。

当“挂逼”状态都不可持续时,饿了几天肚子的大神们,才会再次起身,打个临时工。
但渐渐地,他们连日结也不想做。 时长日久,人就像报废了的汽车,再也难以发动。

要搞钱,野路子依然有。
卖血、卖手机、卖银行卡,甚至以80—150元的价格贱卖身份证。

在庸常生活的巨大陀螺上,失去身份的大神被离心力甩得越来越远。
无可变卖的时候,他们会铤而走险给非法企业做法人。或者 “撸小贷”,一不留神背上数十万债务。

朝不保夕的日子教会了大神抱团取暖,
三和的QQ群、贴吧里,时常有饥肠辘辘的人求救,可怜巴巴地讨一个盒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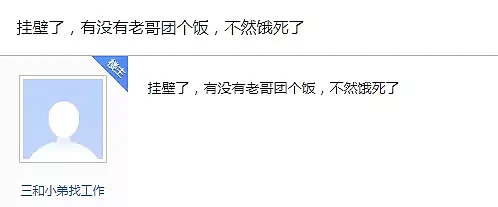
团饭失败,又不愿意开宝箱(翻垃圾桶)的老哥,常常会饿到昏厥,瘫在大街上进行光合作用。

这样的生活状态,让猝死变得稀松平常。
当网吧里有人被盖着白布擡出来,三和大神从四面八方涌来,挤满整个街道。

为彻底挂逼的老哥夹道送行,已经成了这里“不成文的规矩”和“最后的礼仪”。
每个围观的大神都心有戚戚,不知道下一个被“送行”的会不会是自己。

大神是怎样练成的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大神也不是一天练成的。

作为四肢健全的年轻人,最初来到深圳,大多也怀揣着淘金梦,希望能够打拼出一片天地。
但很快,他们发现一切都跟预想的不一样。
进厂以后,日复一日的机械性流水线,每天十几小时的体力压榨,扑灭了身上的青春火焰。

身心一天比一天疲软,而工资,却不见长进。
他们想到自己的父辈,几十年的岁月全都投掷在车间,任劳任怨地接线路、拧螺丝,攒够钱了回到农村、盖房子、生孩子、老去。
对能够接收到更多信息的年轻一代而言,这条道路显然丧失吸引力。
为了逃离现实巨大齿轮的暴力碾压,他们终日聚集在三和,徘徊,张望,流离失所。

比起大战黑厂的艰难辛酸,“做一玩三”的日结模式让憋屈的灵魂重新舒展。
他们忘掉前途、未来,在虚拟的网络世界里结婚生子,称王称霸。现实的种种烦恼,全都抛诸脑后。

当初离家是为了挣钱,如今在城市的夹缝里苟且偷生,家乡自然也成了不愿回首的闭塞之地。
30多年前,他们的父母来到这片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谋生,成为第一代农民工。
如今,他们成为了第一代大神,睡在父母曾铺就的马路上。


“我恨三和,但终究离不开它”
在成为NHK的三和纪录片拍摄对象时,宋春江已经很久没有正经吃过饭了。

他的人生轨迹在三和颇具代表性。
混迹多家大厂,但都坚持不下去。后来陆续尝试过会所服务员、保安、治安员等职位,共同点是累,工资低,且枯燥乏味。
生活没有起色,他很快就腻了。
 流落到三和,低廉的物价让他心醉神迷。
流落到三和,低廉的物价让他心醉神迷。
泡在网吧几个月,为了买游戏装备,他在网贷平台贷款3万,希望卖号赚钱,但碰上账号被封,他血本无归。

贷款还不上,他索性扔掉手机卡。后来身份证也卖掉,被人拿去办了3家非法公司,注册资本1500万。
为此,他经常调侃自己是身家千万的大老板。
“去年,我还有一点点斗志。今年,一点也没有了。”

意志力这玩意,很多人以为有开关控制。关个几天,隔段时间还能再打开。
但实际上,它会锈蚀、腐化,等过了某个临界点,还会“叮”的一声骤然断裂,然后人就被强大的惯性拖拽着前行。
对此,经常与宋春江混在一起的李磊和赵伟也深有感触。
“来了这,你会越来越懒,越来越不想干活,到最后,你会离不开,就像吸毒一样。”

纪录片播出以后,宋春江做直播赚了钱,渐渐还清债务,还回老家补办了身份证,天南地北的观众通过直播鼓励他,希望他早日上岸。
这些说教给他莫大压力。
他算过一笔账,就算一个月工资5000块,在老家盖栋房子也要20多年。
太慢了,他不能坚持。
而且直播也挺折腾,他没有才艺,只能尬聊,总觉得对不起观众。在被人污蔑是团饭狗以后,很快又把手机卖了。
那点人生转机被时间抹平,像从未出现过一样。

离开三和真的很难吗?
是的,很难。
但这难处不在于没钱,没身份证,而在于已经瘫痪的精神世界,再难重建。
回到那个异常闷热的夜晚,在挂逼餐馆里,记者问宋春江,
你还有梦想吗?
宋春江嬉皮笑脸地答道:“回不去了,真的回不去了,梦想,早没了。”
“那你老了以后怎么办?”记者又问。
宋春江抖着腿,苦笑一声,很快又摆出那副浑不吝的姿态:
“老了......就死了呗,没办法。”

说完他咧嘴大笑,其他人也跟着哈哈哈。
笑声碰在一起,都是梦破碎的声音。

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大神”
说起三和大神的挂逼生活,很多人都是抱着猎奇心态,居高临下地怜悯或者批判他们。
但实际上,我们和大神之间,距离真的很远吗?
恐怕并没有。

去年下半年,我在一家狼性十足的公司工作。
公司离住处较远,加上地铁站限流,每天必须六点半以前起床,才能勉强保证不迟到。
高峰期的地铁像一只只巨型怪兽,成千上万的人在怪兽体内碰撞挤压。
面容狰狞地憋个几十分钟以后,精气神被抽走,汗水逐渐发酵,体味交叉感染。
地铁车门打开,人们就像它的排泄物一样,连绵不断地涌出。

出了站,被大太阳一晒,感觉整个人快要化开。
进办公室,屁股刚挨上椅子,马上要开早会。
复盘、规划一番后,兵荒马乱地开展工作。
这期间还得应付从天而降的临时任务,假嗨的集体活动……
我们这一代人,大多没有经历过太大的社会震荡,或者背负什么时代伤痕。
但就是无数这样丧丧的细节叠加在一起,已经在无形中将我们挖空。

为工作熬到凌晨三四点的日子里,什么远大理想都被捶扁了。
我对未来失去想象力,最大的心愿无非是睡个好觉。
每次下楼看到房东儿子窝在大厅沙发里玩手机,厌世情绪尤为强烈。
这闲散的状态他可以持续到死的那一天。甚至可以说,整栋楼的租金够他们世世代代都以这样轻松自在的状态生活下去。
而我呢,整天写着贩卖焦虑的文章,不断接受着领导的鸡血,“奔跑”,“突破”,“加油”。
可事实上,即使命跑没了,也不见得能实现多大的跨越。

我们的终点,不过是别人的起点。
带着这个无力的结论,国庆长假一过,我就裸辞了。
像三和大神一样,我不想再做社会化生产机器上一颗微不足道的螺丝钉。
只想掉在地上沾灰,做个与世无争的垃圾。
刚开始真的很爽啊。每天睡到日晒三杆,醒来也像得了无骨病一样,只想在床上瘫着。
被窝是一片柔软的沼泽地,我沦陷在里边,一切都朝着自废武功的方向行进。

也不知过了多久,某天,在朋友圈里刷别人热气腾腾的日常 , 虚度光阴的恐慌突然从四面八方涌了过来。
我开始投稿,觉得闷在家里状态不好,又跑去图书馆写,假装自己跟社会还没有完全隔绝。
广州不知不觉换了季,从秋到冬,寒意渐生。
零零碎碎发了一些稿子,但相比之前的工资,稿费终归是太微薄了。
卡里的存款一直负增长,为了撑久一点,我去朋友家蹭饭,把家里的东西挂到闲鱼上卖掉。
看似自由的我,陷入了相当拧巴的状态。
一方面,已经从散漫生活里品尝到虚妄的快乐。另一方面,又不甘心只满足于这样的快乐。

有天看《奇葩说》,蔡康永讲家里有个晚辈跑来问他,想做个废物,可不可以?
他很为难,说:“如果你觉得做废物是人生最想做到的事情,你就当废物吧。”
但紧接着又说,
“其实人生完成一些事情,很有意思。”
“有一天你如果发现,你什么都没有完成,可是已经来不及的时候,你心中真的没有一丝惋惜?”
“你要把你的人生丢去做废物,你真舍得吗?”

想了很久,我还是舍不得。
在社会上受了锤,我下意识想回出租屋里躺平。
但如果一直躺着,把年少时对人生的种种设想全都摁灭,我可能会被更大的悲伤淹没。
现在回首那段经历,我没法轻易将它定性为颓废或者洒脱。
只是庆幸因为年轻,我还能在中场休息后,重新找到返场机会。

至暗时刻,滑下去还是忍一忍
最近几年,在高压焦虑的轰炸下,很多年轻人都习惯把丧文化、佛系精神搬出来,聊以自慰。
没错,这是一剂很好的麻醉药。但它不应该成为安抚欲望的唯一方式。
即便在三和,也有人试图寻找其他出路。

跟大神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深圳待了18年的陈用发。
早年一起机械事故,夺去了他整条右臂。之后,他用寥寥无几的赔偿金开了一家名为左撇子的早餐店,练习用左手操持一切事务。
这一开,就是8年。

“因为你没有右手了,你不可能老是怨天怨地嘛。”谈到身体的残缺,陈用发已经释然。
“事情只要你想做,总归是有办法的。”
剥鸡蛋,做肠粉, 磨豆浆……他单手操作,动作却几乎一气呵成。

如今他娶了妻,生了女儿,早餐店的生意不错,偶尔还能接济一下远道而来的老乡。
尽管内心深处,他对深圳没有多少归属感,觉得自己终究会是一个过客。
但为了避免女儿成为留守儿童,并且能有在大城市受教育的机会,又似乎还有无限的动力打拼下去。

社会阶层日渐固化的时代,比输在起跑线上更可怕的,恐怕是底层连进入上层的欲望都被消灭。
三和大神走红网络,有人说他们的存在是对庸俗社会价值“一种消极无声的反抗”。
说实话,这有点强行升华的嫌疑。
就像《超脱》里,刘玉玲冲自暴自弃的学生喊的那句,
“不在乎谁不会啊,但要有多大的勇气才能去在乎呢?”


三和大神乍看无拘无束,其实早已被囚禁在隐形的壁垒当中。
生活刚擡起脚,他们就顺势往地上一趴。
这是沉沦,不是反抗。
他们口中的自由,是任由泥潭将自己吞噬的自由。
看不到明天,也看不到其他任何可能性。

活在尘世,每个人都难免被生活摔打。
没有人可以拯救夹缝中的三和大神。我们所能做的,是不让自己变成三和大神。
这其中的关键,
或许就在陷入低潮的时候,是将所有责任推给不公的命运,还是抓紧那些让你负重前行的东西。
这些东西不一定有多崇高,它可能是自我实现的野心,也可能是为了家人、朋友……无论哪样,去承受、去撑住。

哪怕到最后,付出的全部努力,不过完成了普通的生活。
但只要内心的火种还在,小如蝼蚁的我们,就已经战胜了寂寞的命运。








 +61
+61 +86
+86 +886
+886 +852
+852 +853
+853 +64
+64


